*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國政治理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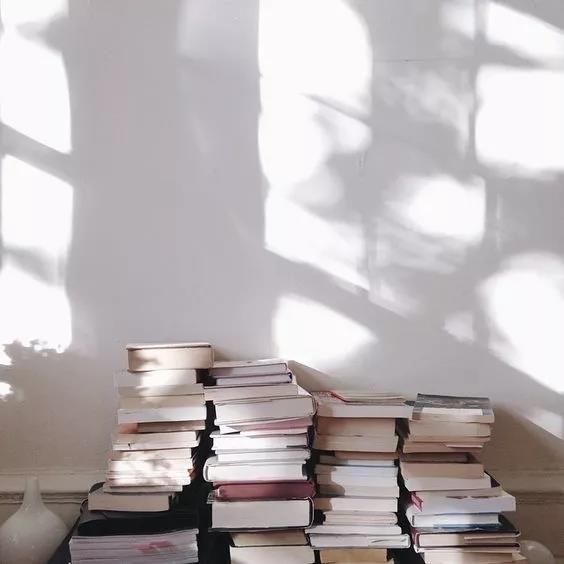
漢娜·阿倫特有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因為智慧,更因為勇氣。在參加了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后,她史無前例地提出“平庸的惡”這一概念,挑戰了人們對戰犯的慣常評價,也讓自己深陷于巨大爭議。有人說,你可以不這么寫的。她卻說,我不可能以第二種方式寫。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我們終于在阿倫特誕辰110周年之際等來了這本書的簡體中文全譯本。
以責任和判斷去愛這個世界,是阿倫特教給我們的最好的事情。
01
艾希曼是誰?
他是臭名昭著的納粹戰犯,屠殺了580萬猶太人,雙手卻沒有鮮血。
“我會笑哈哈地跳進我的墳墓,因為一想到我已經處理掉500萬猶太人,我就感到到極大的滿足。”
這名“納粹劊子手”,官階并不高,只做到中校。但他的工作是,負責執行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最終方案”。
在艾希曼的組織下,整個歐洲的猶太人被運送、收容,最后被集體屠殺;在艾希曼的監督下,奧斯維辛集中營如同一條高效的生產線:每天殺害12000人。
戰爭結束后,艾希曼被美軍俘虜,但之后逃脫。經過漫長的逃亡,他流亡到阿根廷。
1960年,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將其綁架,并秘密運至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審,起訴罪名為“反人道罪”等十五條。
02
阿倫特在現場
得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后,阿倫特向《紐約客》雜志主動請纓,親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審判現場進行報道。
出發前,阿倫特在給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信中寫道:“你會理解我為什么要報道這次審判,我沒能親眼見證紐倫堡審判,我從來沒有見過那些人活生生的是什么樣子,這也是我唯一的機會了。”
阿倫特在法庭上見到的”活生生“的納粹戰犯是什么樣的呢?
“他中等身材,體形較瘦,四五十歲的樣子,前腦門半禿,牙齒不太好,近視眼,脖子干瘦。整個審判過程中,他一直朝法官席的方向探著脖子(從未面向觀眾)。”
“你聽他說話的時間越長,就會越明顯地感覺到,這種表達力的匱乏恰恰與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確切地說,他不會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問題。”
“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麥克白,更遠遠不具備查理三世那種“成為惡棍”的決心。除了不遺余力地追求升遷發跡,他根本就沒有別的動機;就連這種不遺余力本身也沒什么罪,他肯定不會殺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
用大白話說,他只是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做什么。
03
如果人人都獻出一點惡
阿倫特發覺,被關在玻璃籠子里的兇殘戰犯,怎么看都是一個普通人。
她記錄之下的艾希曼,就是為納粹制度效力的一顆齒輪:官僚心態,盲目服從,麻木執行。
正是這一點,令阿倫特意識到,惡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惡魔,在極權主義統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判斷力,每一個普通人都可能成為惡的代言人。
“平庸的惡”這一高度原創性的觀點,由此在阿倫特有關艾希曼的審判報道中被首次提出。
“如此的遠離現實、停止思考,對一個人造成的災難可能要比這個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惡動機加在一起還要嚴重。實際上這是人們在耶路撒冷學的一課。”
不思考,注定了艾希曼成為那個時代最大惡極的罪犯。
因此,阿倫特認為,唯有始終應該堅持辨別善惡的能力,堅持傾聽內心的道德律令,個體才有可能在極權主義統治下抵御“平庸的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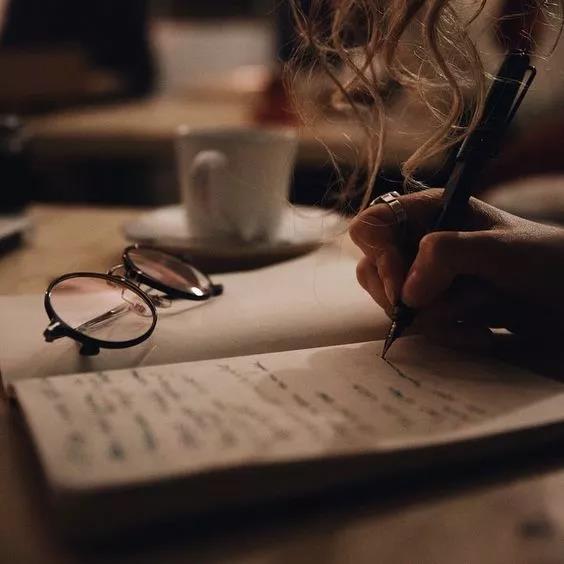
下一條:路徑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