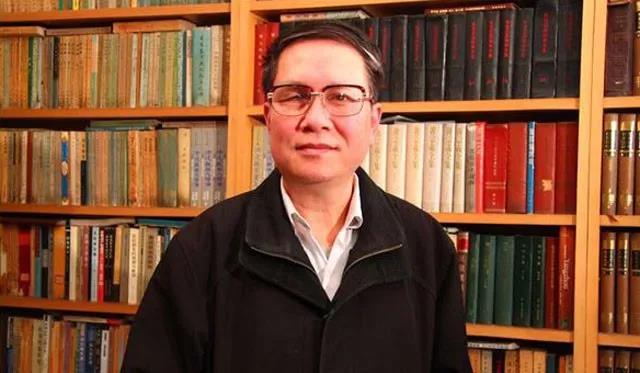
無知小子:秦教授,請您具體解釋一下文化多元化的概念?
秦暉: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費孝通先生曾經講過這么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我以為這就是所謂文化多元的很好的表述,講得簡單一點,也可用中國古代先賢的一句話,就是“和而不同”。有學者質疑曰:西方人要普及自由主義,他不會允許你與之“不同”的。但又有人提出:每個人之間都可以“和而不同”,這本身不就是自由主義嗎?可見,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不同”的單位究竟是什么?有人主張,民族與民族之間可以和而不同,但卻主張在一個民族內部實行強制原則。這當然是不行的,所謂的文化多元就是價值觀的多元。價值評判的器官是大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維能力,普天下皆同。若認為某個民族適合于一人一腦,而另一民族卻需是“共腦人”,似無此理。“和而不同”當然是指每個人之間的和而不同。
一個民族當然會有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特殊價值偏好,但其所以如此,不是因為這個民族的成員之大腦構造與別的民族不同或這個民族喜歡共用一個大腦,而是因為(由于歷史、環境等原因)這個民族的每個人或多數人各自的某些價值偏好(無論是衣食住行,還是在形而上層面)有共同之處。換言之,“民族偏好”是其每個成員個人偏好的“最大公約數”。例如有些人說:西方人尚能,而中國人尚賢。怎么證實或證偽這個說法呢?當然不能憑某中國人或西方人寫過的一本鼓吹尚賢或尚能的書,這樣的書和相反偏好的書在很多民族中都會有人寫,也不能看某個民族的當權者是否把這本書掛在嘴邊,而只能是看生活中一個個具體的人是否確實表現出這樣的偏好。
在與其他民族比較時,只有在可比場境下才能體現出這種差別。例如,如果一個民族自由選舉出了能者,而另一個民族的“賢者”卻是強權自封的,即便后者是真賢,也很難說這里有什么“文化差異”──因為后者的上臺與人們的“偏好”并無關系。可以說這里有“制度”之別,卻不能以此證明什么“文化”之別。而在自由選舉的場境中,若一個民族的選民偏好于選擇賢而未必能的人物,另一個民族的選民偏好于選擇能而未必賢者,這種“文化差異”就得到了證實。甚至如果當選者自稱己賢而其實未必,你可以說選民受騙了(因此下次不會選他),卻不能否定這種“文化”的存在,因為的確是這種偏好使他當選。中國歷史上的帝王無不自稱賢明,這并不能證明“中國文化”尚賢;而明清之際大儒們多有“凡帝王者皆賊也”之論,這也同樣不能證明“中國文化”不尚賢。
可見,一種“文化”是否尚賢,關鍵是看這種“文化”中具體的人是否自由表達出“尚賢”的偏好。同樣,一種文化是否崇孝,也要看這種文化中的個人在沒有父權強制的狀態下能否孝敬父母。“五四”時代有人攻擊啟蒙者“討父仇孝”、毀滅中國文化,陳獨秀答道:“我們不主張為人父母翁姑的專拿孝的名義來無理壓迫子女兒媳的正當行為,卻不曾反對子女兒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說孝是萬惡之首,要去仇他。”(陳獨秀:《辟謠:告政學會諸人》,《廣東群報》1921年3月18日)這道理是顯而易見的:真正的孝敬決不是父權壓迫出來的。真正的“集體主義”也決不是“禁止私有制”禁出來的。一切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它能凝聚人心以抵制外部之強制同化的同時,本不需要在自己內部搞強制同化。文化多元化必然是“文化際”多元化和文化內多元化的統一,“和而不同”、“各美其美”不僅應當是“文化間”關系的準則,而且更應當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內部人際關系、不同價值之關系的準則。事實上就其原意而言,“和而不同”這個古訓在我們的先人那里也確實是就個人之間的價值多元而言的。古代先賢在“華夷之辨”這類文化間問題上一般都主張以華化夷,很少人有華夷價值平等的主張。“和而不同”本是主張華夏內部各種學派、思潮、觀點和價值偏好應當“各美其美”,真正愛好中國文化的人不會不知道這一點!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多元化就意味著“自由優先于文化”。
網友:請問,中國的茅盾文學獎能否也走向世界,去評一評西方人的作品?
秦暉:我覺得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在事關人文價值的領域,既然提倡多元化,就應該允許以不同價值為基礎的評獎同時存在,我相信那些符合人類普世價值的評價會在這種評獎的競爭中表現出最大的感召力。
閑話閑說:秦教授,如何才能保證“自由”在“主義”之前或者之上?在完全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中國,究竟有無可能做到?
秦暉: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想大家其實都知道,問題只在于實踐。所謂實踐當然是指改革進程。
閑話閑說:秦教授,我的問題還有后半部份,在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中國,那樣的改革是否可行?
秦暉:我認為把“傳統”過于凝固化是不合適的。所謂的自由主義若是指哈耶克等人的大部頭著作,那么西方人為自由而斗爭時他們也沒有;若是指人類對自由的一種本能追求,這是普世相通的。一位朋友寫道:“小時侯我是酷愛自由的,決不愿意被家長關在屋子里,而是在田野、山上、河邊到處跑。我也是酷愛平等的,不論是哥哥多吃多占,還是老師厚此薄彼,我都堅決反抗……我愛競爭,總想木秀于林;但也愛合作,害怕離群索居。而競爭與合作在競爭性兒童游戲中得到了和諧的統一:那就是大夥兒都必須遵守公認(即大家同意)的游戲規則。誰不愿意遵守游戲規則,他可以不參加游戲。他如果既要參加游戲又不遵守規則,那么大夥兒就要開除他。完全可以說,這些競爭性的兒童游戲規則充份體現了自由和平等、自由和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高度統一。但是這些規則有時也遭破壞,而破壞規則又沒法開除的人,就是隊長的二兒子。記得有一次我力主開除他,被他擰掉我一個手指甲。”這位朋友說,父親知道他得罪了隊長兒子,非常恐慌,把他打了一頓。從此他慢慢明白了有些東西是需要害怕的,“自由的傳統”便慢慢萎縮了(楊支柱:“被閹與自宮”)。這段大白話比許多關于“自由”的高深理論更耐人尋味。
我也曾舉過一個最淺顯的例子:如果監獄不上鎖,里邊的犯人都會跑掉,恐怕中西各國概莫能外;但事實上有些人卻寧可呆在監獄里,假如他們覺得這樣更有保障的話。換言之,人們可能為“安全”而犧牲自由,這其實也是中外皆然。因此,實現自由的過程,既是擺脫束縛的過程,也是失去“保護”的過程。假如一個體制既沒有束縛功能也沒有“保護”功能,就無所謂自由不自由;而如果一種體制的束縛性和保護性都很強,則人們自由的意愿最小(留戀保護),而自由的阻力最大;如果保護性很強而束縛很弱,那么爭取自由較容易,但自由的代價(失去保護)也會很高;若相反,束縛很強而沒有什么保護功能,人們就會更加向往自由,但也更難得到它。在我們的舊體制中對農民的保護恰恰是很弱的,因此中國農民追求自由的動力很強,小崗村農民那種集體按血手印、冒死沖破束縛的勇氣就是東歐的農民所沒有的。
華山劍:一問秦暉:現在,不少輿論都認為你是與新左派對立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你崇拜西方嗎?
秦暉:過去許多新左派朋友喜歡引我為同道,因為我強調社會公正比他們早得多,他們在文章里常引我的話來批評別人。但我認為,我的立場很清楚,這就是我在《問題與主義》一書序言中講的:我贊成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都認同的那些價值(我稱之為共同的底線),而反對他們都反對的那些價值,至于前者贊成后者反對、或者相反的那些價值,在目前的中國都還不是“真問題”。
華山劍:這是典型的外交語言,秦暉可以去當外交官。
左宗棠:一旦那些問題成為真問題,就表示中國走上正道了。
秦暉:的確如此,在發達國家,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爭論的核心問題是“自由競爭還是福利國家”。但在我們這里提出這種問題簡直是笑話!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既缺少遷徙、就業等最基本的自由,也幾乎完全沒有社會保障。他們缺少自由難道是因為社會福利太多?他們毫無社會保障難道是因為太自由了嗎?西方的自由派與社會民主派之間的爭論在這種狀況下能有什么啟發?如果中國像發達國家如今那樣,人們的自由只受到福利制度的限制,人們的社會保障只受市場競爭的影響,中國可不就走上正道了嗎?講了這點常識就“可以去當外交官”?中國的外交官就這么廉價?“華山劍”先生把中國工農的疾苦當作“外交語言”,他以為自己是哪國人?虧他還自命為“中國文化”的衛道士!
理氣合: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文化一元化。同意嗎?
秦暉:怎么會呢,我們今天的經濟比改革前無疑是更多地趨向于全球化了,但我們的文化也更加多元化了,改革前我們倒是閉關自守的,也是文化(不僅僅是文化)高度一元化的。
華山劍:二問秦暉:你認為當今世界是經濟一體化而文化多元化,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規律是相反的嗎?
秦暉:上面我已回答了這個問題。你不說“全球化”而是說“一體化”,似乎既是“一體”,就與“多元”相反。其實你當然明白有各種各樣的“一體化”。過去鼓吹“一體化”最起勁的是蘇聯控制的經互會,那是計劃經濟的“一體化”。計劃經濟伴隨著“計劃思想”、“計劃文化”,連思維都統一“計劃”了,當然不可能有“文化多元”。如今的全球化實際上是經濟市場化,市場經濟當然有它的毛病,但它的好處恰恰在于它與上述那種“經濟一體化”“相反”,因而恰恰與文化多元相通。市場經濟講究競爭,而文化多元化不就是要“百家爭鳴”嗎?怎么能說這兩者“相反”呢?有人說這樣就叫“西化”,其實“西方”以前恰恰不是這樣的。中世紀的西方不僅談不上“全球化”,就連一國之內的經濟也非“一體化”。那時經濟上是領地、行會層層割據,文化上是神權專制,哪有“多元”的影子?從那種狀態走出來,即走向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這個過程并不始自今日,實際上它就是“現代化”的另一種說法。
藍淵:請問秦教授,中國文化的優點在吸收同化,西方的文化優點在競爭與排斥,長遠而言,誰勝?
秦暉:我對這種說法本身持懷疑態度,也許不同的“制度”在吸收、競爭等方面有不同的表現,但很難說做為民族標識的“文化”是排斥競爭的或拒絕吸收的,“西方文化”如果不吸收其他文明之所長,能有今日之成就嗎?中國人今日在商戰中的競爭表現不也很出色嗎?
燕人楚源:秦教授,我也非常贊同“和而不同”,但我對其能否實現表示憂慮。比如現代中國的回族、滿族等少數民族已幾乎完全被漢族同化了,還能保證其本民族文化得到發揚光大嗎?鄭重聲明:我絕不是民族分裂主義者。
秦暉:我認為,“和而不同”是以公民個人的自由選擇為基礎的,因此,“和而不同”就是要反對強制同化,而不是“強制反同化”。不管那個民族的任何人,他如果欣賞“別的文化”,別人不應當干預他,當然這是在法制允許的范圍內;但如果他不欣賞,誰也無權強制他,包括強制他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在內。
燕人楚源:秦教授,提一個稍尖銳些的問題,我注意到您在“回答《詢問》”一貼中在“本民族”三字上加了引號,這是否表明您對少數民族有看法。您有權不回答,但我認為作為一個治學之士,肯定能夠坦然面對一切事物,不是嗎?
秦暉:我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什么東西可以稱為“本民族”的,本身或許就存在著不同看法,不管是少數民族或漢族,這一點都是共同的。所以我想,一個人如果要代“本民族”立言,特別是如果他又是針對自己的同胞提出某種限制,那還是需要謹慎點好。
華山劍:三問秦暉: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是不是書生的臆想?你怎樣解釋現在美國的話語霸權現象?!
秦暉:經濟一體化與文化多元化都是個“正在進行時”的過程,既不是臆想也并未完全實現。至于你講到的“話語霸權”,如果是指一種強制,那不管是美國的或是任何國家的,我一律反對,但如果一種價值被跨“文化”地自愿普遍接受,那么我想,它很可能體現了人類的普遍追求,不能說是那一民族的專利。
華山劍:四問秦暉:你認為現在存在美國文化霸權現象嗎?如果存在,你是否支持中國文化在世界走強?
秦暉:目前在很多領域的確存在著“美國文化的優勢”,其中很多東西我并不喜歡,如麥當勞、好萊塢等,我希望中國能拿出高水平的“文化產品”來贏得與他們的競爭。但是,每個中國人具有選擇或不選擇麥當勞等的權利,屬于人的尊嚴,而決不是“某個文化”的特有表現。中國人應該有這種尊嚴,如果連這種尊嚴都沒有,我們首先就沒有擺脫“人身霸權”,更何談擺脫“文化霸權”呢?
燕人楚源:鄙人在此提出幾點拙見,不自量力與秦教授討論。我認為今天的世界名為文化多元化,實則文化一元化也。西方所謂“強勢文化”作為強權政治的伴生物強力滲透到世界的每個角落,世界人民普遍接受了西方價值觀,一味以西方之標準來衡量事物,這是造成當今世界物欲橫流的重要因素。君不見,民族虛無主義日漸抬頭,把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一概斥為糟粕。我不否認東方傳統文化中有很多糟粕,但應該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在華夏文明中,尤其是在思想領域,還是有很多瑰寶的。但現在的現實卻是世界文化趨同,一致向西方看齊,使得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常言道:一花獨放不是春。只有百家爭鳴,人類在思想文化領域才會有希望。而現在的人類眼中似乎只有利益,這是令人悲哀的。不知秦老師如何看待此問題。
秦暉:我覺得您對“文化”的理解可能有問題。打個比方說,儒學、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應當多元并存,但異端審判與信仰自由可以并存嗎?若異端審判仍然存在,則前三者就絕無可能并存;如果前一種意義的“文化”要多元并存,我們就只能贊成信仰自由,而不能容忍異端審判。我不知道你所謂的“西方文化”是指基督教還是異端審判?若是前者,我認為它遠未一統 TianXia;若是后者,那么正是西方人自己最先拋棄了這種“西方文化”,當然就更談不上它的“一元化”了。奇怪的是,對異端審判這類的“西方文化”,許多非西方人反而更為戀戀不舍。
進而言之,何謂“西方價值觀”,它與西方人的強權利益是什么關系,西方人是否就那么喜歡別人也“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事物”,也都還是個問題。例如,當年西方殖民者在非洲販奴掠奴,罪惡很大,可是西方人(白人)內部早已普及人權,禁止了奴隸制。后來黑奴們起來奮斗,爭取人權(當然不是什么“非洲式的人權”),要求得到與白人平等的地位(“一致向西方看齊”?),并取得了歷史性勝利。現在我要問:黑人爭取的自由民主人權僅僅是“西方價值觀”嗎,還是一種普世性的人道主義價值?黑人要求自由平等,就是屈從“強勢文化”、“一味以西方之標準來衡量事物”,而俯首帖耳甘心為奴反倒是抵制“文化霸權”、拒絕“西方價值觀”的壯舉嗎?
顯然,這些問題只可能有兩種答案:或者自由人權等等是普世價值,因而不存在屈從“西方價值觀”的問題;或者視那些東西為“西方標準”,但即便如此也應注意到,它本身與西方人即白人的霸權利益也是沖突的,而不承認白人人權標準適用于黑人的“雙重標準”理論才是霸權利益所需要的。從南非廢除種族主義的過渡期可清楚地看到,正是專制的“黑人家園”傳統勢力和“祖魯文化復興運動”(因卡塔)與白人政權聯手阻礙著黑人的解放,而似乎更為“西化”的非國大則領導了這場解放。歷史上這類事真是太多了。
網友:秦暉是故意和我們玩瞇眼游戲,麥當勞怎可與哈耶克相比!我是在問西方思想文化的霸權!
秦暉:可比不可比,看你談的是什么問題。在生物學中人與老鼠是可比的,在倫理學上就不可比了。在人們可以選擇和不選擇這一點上,麥當勞為什么不可與哈耶克相比?你有不贊成哈耶克的自由,別人有贊成的自由,這與選擇不選擇麥當勞難道有什么不能類比的區別嗎?我倒很想知道,在我們現在討論的語境中,所謂麥當勞與哈耶克不能類比的含意是什么?是說我們不禁止麥當勞但要禁止哈耶克呢,還是不禁止哈耶克但要禁止麥當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弘揚中國文化時,先賢這句寶貴遺訓也不該忘記吧。
豐臨:文化多元化的前提:多元中的每一元趨于成熟;多元文化之間可平等學習和討論;多元文化有共同遵從的基本原則;基于人的發展的價值評判;任何一元文化都服從于個體的自由選擇和幸福;以人的進步為社會進步的衡量標志;多元文化共同致力于人類進步和人的自由幸福;實現沒有任何特殊的一元文化;任何一元文化都是可以討論的;不立足于人的發展的偽文化沒有生存空間;任何一元文化都是該文化主體中人的自由選擇和討論的結果……
秦暉:我同意你的看法。尤其是“不立足于人的發展的偽文化沒有生存空間”說的極好!如今的確有一種只愛“文化”不愛人的怪現象。有一篇文章大罵農民流動毀壞了“鄉土中國文化”,另一篇甚至把公路與廣播都看作是對“本土文化資源”的威脅。一些人張口“文化”閉口“民俗”。其實,有民才有俗,關心民俗,歸根結底還是要關心“民”、關心人。然而如今對民俗感興趣的人,包括藝術家與學者中,不少人卻是心里既無“民”,眼中惟有“俗”。一些人把貧困當作牧歌來欣賞,甚至提出應該把某種“文化”當作標本封閉起來,以免外來影響破壞了這種現代人樂于欣賞的“風景”。這樣的“民俗”作品縱然能時髦一時,終究是沒有真正的生命力的。
華山劍:六問秦暉:如果你認為世界應該文化多元化,而現實是西方文化過強,那你的文化立場是否應在中國一邊!
秦暉:如果你說的“西方文化”過強,指的是基督教、麥當勞等,那我可以說,我希望并且力爭“中國文化”在多元中崛起,會為此竭盡全力。如果你是指的中國公民如今享有的權利太多,那么我希望你容忍這一點,看在你是個中國人的份上!即使你認為這種權利是一種“西方式的”權利而討厭它,你完全可以不去行使它,但你無法剝奪別人的權利。就算是“西方式的”權利,但它是我們的同胞在行使,并不是“西方人”的治外法權,更與“西方文化霸權”無關。相反,如果是“西方人”行使了“中國式的權力”(比方說秦始皇式的權力),那才是真正的西方霸權了。你說呢?我常常納悶:為什么我們有些“中國文化”的弘揚者喜歡在自由、民主、人權等領域豎起“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禁牌?為什么正是他們,喜歡拿西方中世紀的人權標準來強加于自己的同胞?
存在與虛無:請問秦教授:您如何評價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您對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光榮革命作何評價?
秦暉:關于“第三條道路”一書,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文章的題目“‘第三條道路’還是共同的底線?”反映了我的觀點,登在《世紀中國網》上,請你指教。至于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若作詳細評論就說來話長了,我認為他們都有寶貴的遺產值得繼承,也有教訓需要吸取。最重要的一點是:至少在自由秩序有待爭取的時代,“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應當是互補的,而不是互斥的。
燕人楚源:文化多元化就應該允許人們自由選擇,這是你我共同的觀點。而我在“討論”中想說明的也正是此點。比方說,有人愛吃面包,有人愛吃餃子,這純屬個人口味,無可非議。如果有一天絕大多數人都只吃面包了,這正常嗎?
秦暉:這要看他們為什么“只吃面包”。如果有人不準他們“吃水餃”,那我們要跟這個人拼命;但如果是自己愛吃,就隨他們去好了,反正我是不吃的。
燕人楚源:我剛才是想說,如果人們都是自愿選擇“面包”(西方文化)的話,當然無可非議,但現實情況并非如此。西方文化的走強是強權政治帶來的結果,因此可以說是無形中變相強迫人們接受,而并非完全因為“面包”比“餃子”好,這就值得警醒了。您怎么看?
秦暉:強權政治在國際政治領域當然是存在的,這就是我前面談到的“國家利益”的沖突。道理很簡單,任何權力都有越界的可能,關鍵在于有制約它的機制,即民主機制。目前人類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內已找到了建立這種機制的方法,這是我們應當學習的,全球化恰恰為這種學習提供了方便。而在國際領域確實還沒有這種機制,所以全球化不會消滅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我們需要捍衛國家利益,但這與在一國范圍內消滅強權政治、實行公民政治,應該是并行不悖的。
華山劍:七問秦暉:你主要的學術思想資源和立場是中國還是西方?如果是西方,你是不是在對西方錦上添花!
秦暉:我的思想資源既有中國也有西方的,但這并不重要,關鍵在于這些資源有利于人類,因此也就有利于我們中國人。其實,我所運用的“資源”恐怕更多的是屬于一些常識,無論中西皆通行的常識。可惜的是,這些常識有時被人遺忘。
閑話閑說:您如何看待哈耶克為自由所作的界定及他的自由秩序理論?
秦暉:其實我對哈耶克的思想是有不少保留的。我認為他面對的問題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全部理論基本上只是講我們不能做些什么,以免失去自由,而不講我們應當作些什么,以便得到自由。顯然這并不是我們面臨的基本問題,哈耶克沒有寫過《通往自由之路》,這不能苛求于他。但我們因此也就不必把他當作神來崇拜。我有兩句話:一句是“主義”可拿來,“問題”需土產,“理論”需自立;另一句是,弘揚“普世價值”,慎言“普世問題”。
唐漢:請問你對中國文化與現在普遍倡導的全球化概念如何看待?中國文化如何面對全球化的沖擊,從而得以與美國或美元文化相抗衡,甚而稍稍地領先?
秦暉:我以為,所謂中國文化最深刻的內容,與其說是只有一部份中國人講的、甚至是光講而不做的某些書籍,不如說是真正代表五千年來一以貫之的那些民族特點,如作為單音節詞根語的漢語和作為形聲字的漢字所導出的那些思維方式,這些方式在新的世界上也許會有以前未曾發揮出來的活力。簡單點說,我認為英語的霸權(這可能是如今名符其實的一種“文化霸權”)在信息化進一步向縱深發展的時代會遇到挑戰,單位符號信息量更大的漢語是更有希望的。
其次,與包括西方主要語言在內的其他語系相比,漢語(以及漢藏語系的若干語言)有個獨一無二的特點:它的每個音節(“字”)都有其獨立的語義,構成所謂的詞根。而西方語言沒有“字”的概念,只有純粹表音而無語義的“字母”,若干字母組成“詞”才有了語義。如果說,每個音節都有獨立語義的這種語言能影響思維方式的話,它是有利于形成“每一個個體都有獨立價值,都是獨立的意義單元”這樣一種觀念的。盡管“文化決定論”不能成立,最能保障個體意志自由的制度也不是我們首先創立的,但中華民族在這方面的創造力也不可低估。中國人建立過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如今中國人在一個地區創造的民主憲政轉型也比世界同類地方更成功。因此,那種以為“文化劣根性”決定了中國人只能當奴才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至于中國人在市場經濟中表現的“商戰”才能更是世所公認的了。香港、新加坡這些地方不只是GDP增長快,經濟自由度也連年居世界頭幾位,超過絕大多數歐洲國家。
每個音節都有獨立語義的漢語有利于培養個性(只是“有利于”,并不是說講漢語者都有個性),而作為形聲字的漢字又有利于培養凝聚力。由于漢字不是拼音文字,方言差異極大的中國人仍能擁有共同的書面文化,避免了古羅馬文化因拉丁語的方言化而消失這類其他文化常見的命運。這過去造成了中國文化的“連續性奇跡”,今后這種書面文化統一性形成的凝聚力仍然有利于全球化時代中國人的發展。
網友:中國人也許有盲目崇拜麥當勞、肯得基等洋貨的心態,這種心態說明中國人的思想很難獨立自主。
秦暉:如果你認為“盲目”(其實我也這樣認為),你可以評論或規勸,但不能強制。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對不影響他人自由的某個人的“盲目”選擇予以寬容,否則這個社會就只有“英明者”的活路了。
燕人楚源:請問秦教授,您是否認為有一條龍身上雖然有很多歷史遺留的沉疾,但也不乏燦爛之處呢?如果是,我們為什么不應該批判地繼承和發揚呢?
秦暉:“批判的繼承”當然是絕對正確的,問題在于批判什么?繼承什么?如果把“文化”理解為某種學派、典籍的話,我以為以往我們的遺憾可能不在于批判過多或繼承過多,而在于可能批判了一些不該批判的或是批判過份,同時又繼承了一些不該繼承的。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我以為它的局限性(它的功績這里就不說了)與其說是過于激進或過于保守,還不如說是:它在反儒這一點上過于極端,而在反“法”(法家專制傳統)上又遠遠不夠,以至于后來出現了那場“批儒弘法”的災難。實際上中國以往“罷黜百家”時,真正“獨尊”的何嘗是孔孟的那種“儒術”。所謂性善論、仁治說、倫理中心主義不過說說而已,“百代都行秦政制”才是真正的傳統“硬件”,而“軟件”則如王夫之所言:“上有申韓,下必佛老”,有權者行“法術勢”而指鹿為馬,無權者圓融通透而“難得糊涂”,致使性惡論、厚黑學、權力中心主義和“儒之吏化”泛濫成災,形成“法道互補”之弊。儒家雖然不是什么“超越現代性”的救世法寶,卻也并非中國進步的主要障礙,除了“民貴君輕”、“因民所利”、“不欲勿施”和“有教無類”等資源如今仍具有生命力外,原初儒家的小共同體本位取向至少在現代化進程前期也不是壓制個性自由的主要問題,相反,它在與“西學”會融后(這一點至為重要!非此則儒學難以走出“儒表法里”的怪圈)還可能有助于消除法家專制傳統。所以,我在文化上還有一個主張,即西儒會融,以消解“法道互補”(即強權哲學與犬儒哲學的互補)之弊。
肖曉春:教授似乎太樂觀了,弱勢國家和民族既無法拒絕經濟繁榮的誘惑,同時又丟掉了自己的文化具體性和個性。
秦暉:你這個“具體性和個性”說得好,如果我們民族的每個人之“具體性和個性”都能得到寬容和保護,何愁我們民族的“具體性和個性”會受到威脅?但我這里要強調一點,我們今天只是談的文化問題,并不是在談“國家利益”。全球化時代是會有國家利益沖突的,即使文化相同、主義相同,兩國的利益也不會完全一致。但這與文化沖突是兩回事。“文化國粹”的愛好者同時是賣國賊,西學的弘揚者同時是愛國者,這樣的例子還用我多舉嗎?
黃炎:您認為中國人該不該去拿諾貝爾文學獎,比如高行健。我認為高的獲獎是全體中國人的無上榮光,更是中國文化、華夏文化在經歷了百年磨難之后的被世界重視和承認,尤其是西方,他們不承認這個事實不行!你以為如何?
秦暉:據我所知,對高行健的獲獎,不但不同價值觀的人有不同評論,就是相同價值觀的人在這一件事上也有相反的看法。在我看來,高行健獲獎的最大意義并不在于他本人是否最優(我以為不是),而在于人們對這次獲獎所發表的各種自由言論本身。
唐漢:秦教授,請問你對現在的企業文化與校園文化有何看法?我的意思是說,從大學校園出來的莘莘學子很難一下子適應企業文化。您認為,校園文化該如何處理,同時企業文化又該如何發展中國特色?
秦暉:我們現在一般在“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特點”這個意義上使用“文化”一詞,所謂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文化就是這個意思。因此,你講的“文化”與本次討論大多數人講的含義不同,你的問題實際上是對我們目前教育制度的質疑,所謂學校畢業出來無法適應企業,應該就是這種問題。關于教育,我在《問題與主義》一書中有一篇文章“教育有問題,但不是教育問題”談到過,請你指正。
燕人楚源:對“法道互補”的回應。你說得很正確。可問題是大多數年輕人做不到,一味崇西貶中。而老年人又正相反。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
秦暉:我的感覺與你不同。我以為,“法道互補”之弊在各個年齡段都存在,這一輩不見得比上一輩更清。但對“西儒會融”我還是樂觀的,至少不是絕望的。
蕞蕞:請問自由主義如何應對多元主義的進攻?
秦暉:我理解的“自由主義”實質是“自由優先于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本身就是多元主義,談不上應付進攻的問題。我前面已說過:文化多元化,就是“自由優先于文化”。但如果所謂多元主義指的是信仰自由與宗教審判并存的話,那當然是另一個問題。但我以為,信仰自由終將戰勝宗教審判,或者說是可以戰勝后者的進攻的。
真正陷于理論困境的是一些自由主義的批判者。他們一方面以“文化多元主義”為理由,把自由、人權等價值的弘揚說成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化”,另一方面又強調“不允許‘自愿當奴隸’”,亦即主張“強迫你自由”。我以為這兩者是尖銳地矛盾的:假如某一“文化”中人們甘愿人身依附于他們的酋長,那么從文化多元的立場出發,別人不應當去干預他們,更不能“強迫他們自由”。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多元主義必然意味著允許“自愿當奴隸”。但如果人們不再甘愿依附而起來反抗酋長,酋長卻鎮壓之并強迫他們當奴隸,那么按道理別人就應當聲援奴隸的斗爭。這并不違反文化多元主義(既然他們已不愿做奴隸,亦即做奴隸這種價值偏好已不存在,當然就不能說做奴隸還是一種“文化”了),同時也符合自由主義乃至社會民主主義。因此,這兩種主義與“文化多元”并不矛盾。然而照上述批判者的立場,事情便變得很滑稽了:在人們甘愿依附于酋長(亦即該“文化”確實存在)時,這些批判者要“強迫你自由”就勢必破壞文化多元主義原則,而遵守文化多元主義,就只能允許“自愿當奴隸”。相反,當人們不愿依附并進行抗爭(即上述“文化”已不存在)時,批判者卻要求別人不準聲援他們,要看著他們被迫當奴隸,否則就是“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事物”,就是追求文化一元化──換言之,批判者的立場在這里變成了:不允許“自愿當奴隸”,卻允許“強迫當奴隸”!
可見,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文化多元并不矛盾,但“強迫你自由”與文化多元主義絕對是矛盾的。上述批判者既然張口閉口文化多元,“不允許‘自愿當奴隸’”的高調就很難唱下去了。
hhj:西方文化的核心是進取型精神,而東方特別是中國文化則是“無為”型精神,秦暉先生是否同意?進取精神使西方獲得了今日的成就,但同時也致使人類生存與生態陷入巨大危機。而中國的無為精神雖然未能使中國象西方那樣發達起來,但它卻使人類與自然和睦相處。在生態漸漸惡化的今天,中國式的無為精神也很可貴。因此東西方文化的結合應該是最理想的。
秦暉:這種說法以及類似說法在“五四”時代十分流行,當時也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但現在我對這種大而化之的說法持慎重態度。更確切地說,我以為制度的區別比所謂“文化”的區別更重要。
華山劍:將制度和文化區別開來,這的確是秦暉的一大發明!
蕞蕞:你說的也對。制度和文化難道能分離?
秦暉:制度與“文化”能否區別,關鍵在于你如何定義“文化”。改革前我們經常談論“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等。這里所謂的“文化”當然不能與制度分離,它的定義就是某種制度中的“上層建筑”。但這樣定義的“文化”與“民族性”無關,也不是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特徵。所以那個時代的人們是不大講什么“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的。但如果“文化”被定義為民族性,那就必須把它與制度區別開來。道理很簡單:在這種定義下把“文化”與“制度”混為一談,就等于把民族性與制度差別混為一談。仿佛一個民族只能“天不變,制亦不變”地維持一種制度,中國人永遠只能“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而西方人從荷馬時代就有議會民主。我們能接受這種說法嗎?按這種說法,一切改革都不必搞了。如果帝制就是中華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特徵”,那辛亥革命就是毀滅中華文化,孫中山豈不成了民族敗類!
常識告訴我們,基督教、儒家和伊斯蘭教是一種區別,神權專制及異端審判與政教分離及信仰自由又是一種區別。歐洲過去與現在都屬于基督教文化,但神權專制時代與信仰自由時代的制度差異何啻霄壤之別!如果視這些常識“是秦暉的一大發明”,我只能感到悲哀。總之,按照某些定義,“文化”與“制度”可以不加區分,但那樣的話,“文化”與民族特徵就絕對要區別;如果把“文化”當作民族特徵,“文化”與“制度”就必須區別開來。二位網友可以作第一種選擇,但那樣就不必討論什么“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了。不論哪種情況,民族性與“制度”都不能混為一談。
hhj:我是從人類生態的惡化來考慮這個問題的,西方的進取型造成了人類生態的惡化,而中國的無為型則正好可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
蝶之仙:我不同意這樣的將老子、孔子哲學降低為環保理論的觀點。
hhj:當人類因環境問題而滅亡時,哲學是不是應該關注一下環境問題?
蝶之仙:哲學關心環境問題,與儒家道家哲學的本意畢竟不同吧!
秦暉:我國古代的“天人合一”學說,是一種以“宇宙等級秩序”來證明人間等級秩序的理論,它與環境保護本不相干,倒是與文革中那種“天上星星向北斗,地上葵花向太陽,人民心向毛主席”的歌謠同一思維邏輯。如今人們把環保意識附會于它,倒也不無可取。因為,作為符號的語言能指在歷史中增添新的所指,所謂托古改制、借古喻今之類,即或不為學問而僅是宣傳手段,也是有用的。
問題在于,環境保護決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個認識問題。沒有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所謂的“重視環境”只能流于空談。由于經濟學上所謂的外部性,人人明知重要而又人人破壞之的事例不勝枚舉。筒子樓里公共水房往往污穢不堪就是個明例。至于我國古代,無論其“文化”是進取的還是無為的,其環境的紀錄應該說并不好。遠的不說,明代的《徐霞客游記》就記載了贛、浙、湘、桂、黔、滇一帶嚴重的環境破壞,如造紙業污染河流、燒石灰污染空氣毀滅風景、亂砍濫伐使“山皆童然無木”,生活垃圾使永州、柳州等地的許多名勝堙為“污濁”的“溷圍”。那時還未出現尾氣、酸雨和核污染,只是因為古人尚不懂工業技術,并非他們懂得“天人合一”。今日人類面臨的環境危機恐怕也只能主要依靠全球合作下的制度與技術創新來解決。當然,“全球合作”伴隨著沖突與討價還價,各國都知道環保重要,但都想盡量為此少付代價,而只想“搭便車”,發達國家尤其難辭其咎。但這與上述“公共水房問題”一樣,是利益協調機制問題而不是認識問題,或者說是制度問題而不是“文化”問題。“天人合一”的新解釋我很贊成,但只怕作用有限。
唐漢:請秦教授詮釋一下“全球化”的含義──在現代競爭社會──兼作方才秦教授“校園”問題的回應!
秦暉:“全球化”的解釋據說已有一百多種,我無法給出一種標準的定義。但我想,“全球化”應該使我們每個人更有可能實現“我所喜歡的”目標,包括“烏托邦”目標,只要它不強迫其他人。如果是這樣,“全球化”的世界將是更異彩紛呈的世界,其中包括也有反對全球化的聲音這一“彩”。
華山劍:我早就說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大多有烏托邦情調,人們總是不信。這不,秦暉就認帳了!
皮士:新左派的烏托邦情結更濃烈,離現實更遠。
蕞蕞:這里“華山劍”露出馬腳了:1. “我早說過”是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說過的?誰會有這種言說的權利?充當什么樣的角色才會有這樣的言說權力?2. “人們總是不信”,他是向什么人說的,對象是誰?為什么不信?太有必要集結一下“華山劍”的貼子了,一定很有意思。看一看他的“十一問”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秦暉:關于烏托邦與自由的關系,我在“善惡、信仰與自由”、“失去強制的烏托邦”、“自由、烏托邦與強制”等幾篇文章里已講得不少。我的立場是“共同的底線”,因此無論自由主義是一種時髦還是一項罪名,我都既不會刻意自稱是自由主義者、也決不回避別人稱我是自由主義者。我不知道我對烏托邦的看法是不是標準的“自由主義觀點”。有些自由主義者認為烏托邦是災難之源,但也有些自由主義者例如諾奇克,雖然并不追求烏托邦,但明確表示不是反烏托邦主義者。我也許比他們更不反烏托邦。我認為,烏托邦(它的狹義定義涉及復雜的宗教學問題,這里只取廣義,即“不能實現的理想”)首先是無法“告別”的。因為人們不能事先判定什么可以實現、什么不能實現,并只在“可以實現”的范圍內思考。在這個意義上,“告別”了烏托邦,就不再有自由思想者。哈耶克指出理性的局限,呼吁警惕“理性的僭妄”,說得并不錯。但他回避了一個悖論:“理性的局限”應當重視,但正因為有這種局限性,人不可能確定“理性之限”在何處。所以“限制理性”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而限制強制才是既必要也可能的。其次,烏托邦本身也不是什么壞東西。古人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盡善盡美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人們根本不想追求盡善盡美,又何來較善較美?對烏托邦的追求(這里姑且不討論某種具體的烏托邦是否可欲)其實很可貴。如果人們都“現實”到了不敢“想入非非”的地步,那倒糟了。
為何以往在某種烏托邦的名義下常常造成災難?道理很簡單:因為強制。任何“主義”或“文化”,無論它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空想的”還是“現實”的、“中國”的還是“西方”的,作為一種思維活動都只能屬于具體的思想者個人。我可以為我所信的而獻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么并強迫你為“我覺得你應該信”的東西而獻身。任何奉行強制原則的“主義”、“信仰”或“文化”都會面臨如下悖論:如果信仰能夠成為強制的理由,則被強制者不僅無從判斷強制者的“信仰”是合理的還是荒唐的,是可實現的還是“空想”的,甚至也將無從判斷強制者是否真有信仰,從而為全無信仰、只為一己之私而濫行強制者迫害虔誠信仰者創造了最佳條件。莫爾們的蒙難與托爾克維馬達們的得勢就是這一邏輯的結果。要之,“托爾克維馬達迫害莫爾”這種惡現象的原因不在于“空想”,而在于強制;因而除惡之法也不在于“現實主義”,而在于自由。“空想”本身再幼稚,無非是不能實現而已。堅信者本人不惜蹈艱履苦而躬行之,如后來的歐文、卡貝等人之所為,縱使事終不成,也在人生的悲壯之中給歷史留下了一種崇高,卻并未給社會帶來災難。反過來說,沒有“空想”的強制、“現實主義”強制可能造成的禍害未必比“理想主義強制”小──實際上由于強制本身具有消滅“理想”(就像消滅莫爾本人一樣)的作用,一切打著“理想”招牌的強制幾乎都會變成厚黑學家的“現實”利益強制的。
500年前的宗教審判是這樣,500年后的“左”禍也是如此。在中國的“左”禍中,的確有過“右派”被“左派”所整肅、一種“主義者”被另一種“主義者”所整肅的事例,但更多的還是大批“無不同政見者”被借“信仰”之名以營私的政治流氓所陷害冤殺的事例。如今那個時代常被說成是個“烏托邦”的、“理想主義”的時代,其實那時多的只是關于“理想”、“主義”的假話。在“莫爾”遭難、“托爾克維馬達”得勢的時代哪里真有什么“主義”可言!所以,信仰是可貴的,但信仰不能成為強制的理由。“烏托邦信仰”不能成為強制的理由,“現實主義信仰”同樣不能成為強制的理由。說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不是因為后者是“烏托邦”而前者是“現實”的──實際上,“純粹的市場經濟”與“純粹的計劃經濟”大概都是烏托邦,而“不完全市場”與“不完全計劃”都具有現實可行性。然而,“計劃經濟”是“一切行動聽指揮”的強制經濟,“市場經濟”則是自由經濟,它允許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目標,包括烏托邦目標;“計劃經濟”禁止私有制,而“市場經濟”從來不禁止“公有制”,相反它可以使強制地化私為公與強制地化公為私者都難遂其欲。無怪乎一百多年來,各國各派的社會主義者如英國的歐文、法國的卡貝和俄國的格伊恩斯等,都甘愿背井離鄉到那個最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去搞烏托邦實踐,形成所謂“社會主義者愛美國”的傳統。可見,現代市場經濟盡管如其批評者所言,只有“形式自由”而不能令人滿意,但由于它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強制,因此它不僅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率,而且也更人道。
經濟是如此,“文化”等領域亦然。所以,人們才呼喚一個人格獨立、信仰自由的公民社會。這個社會與宗教審判時代的社會之別,決不僅僅是從“理想主義”轉向“現實主義”,或者由“A文化”轉向“B文化”。因此,我向“右派”說,過去的災難不在于烏托邦,而在于強制──強制地化私為公;我也向“左派”說,現在的問題不在于市場,仍在于強制──強制地化公為私。對于“西化”派和“中國文化本位”派我也持同樣態度。我對“告別烏托邦”不感興趣,但要為告別強制而奮斗。我相信這種努力本身不是烏托邦,是可以實現的;但就算“知其不可而為之”,我也相信它不會給人們帶來壞處。對于“華山劍”先生的“反烏托邦”,我只能說:過去人們壓制“自由主義”通常是打著“理想”的旗號,如今則是公開亮出“現實的”既得利益取向了,這正表明我們的努力是有希望的。“華山劍”先生指出了我的理想主義色彩,對此我應當說一聲“過獎”!
燕人楚源:在這里澄清一個概念,我說的文化不是指某些具體的宗教或學派,而是一個民族在產生和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理念,文化就是這種理念的積淀。當然,這種理念有時會通過宗教或學派體現出來,但是是理念創造了學派或宗教,而不是反之。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秦暉:我覺得談論“一個民族的理念”需要謹慎。如果說我們漢族人都自認為是炎黃子孫,這個理念大概是存在的;但如果說我們比其他民族的人更不重視公民個人權利,這個理念就絕不是“民族理念”,而只是一些人的理念;至于說我們民族的理念就是認同孔夫子或其他什么人,那就更成問題了。假如說一個民族要有富于凝聚力的某種共識,那么這種共識只能建立在尊重民族每個成員的權利與尊嚴的基礎上。
烏有莊100號:秦先生能否給“先進文化”下個定義,中國傳統文化是先進文化嗎?
秦暉:人們通常把“文化”定義為“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幾乎是“民族性”的代名詞。這個意義上的“文化”是不能比優劣的,否則等于是說民族有優劣。在這個意義上也就不存在什么“先進文化”。我的基本看法是,“文化不可比,制度有優劣”,因此我贊成文化相對主義,但主張把文化相對主義的命題倒過來講,即“凡是不可比優劣的那些民族特徵就是文化”。如果可以比較優劣,那很可能就是屬于制度范疇內的東西了。
華山劍:唉!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缺陷在這里表達出來了!哲學有高低,文化卻無優劣!哲學不是文化?!
秦暉:這個反問還是上一次的同義反復。哲學如果與制度相關,它就有優劣:法西斯哲學當然劣于民主哲學。如果與民族性相關,它就無優劣:“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就無優劣。不過作為世界觀的哲學歷來是多元的,什么是“民族的”哲學?比如“中國哲學”吧,它是儒家?法家?還是黃老或陰陽?很多人大概會把儒家哲學當作“中國哲學”的正宗,那么中國歷代反孔的人難道是站在“外國哲學”的立場上了?對“文化”這個概念的認識也是如此。
筆者曾提到一種悖論:設若某甲性喜吃米飯、喝老白干,某乙性喜吃面包、喝威士忌,我們可說二人各屬于一種“文化”;若有一人群A都象某甲那樣飲食,另一人群B都象某乙那樣飲食,我們就名之曰文化A和文化B。但如果某一人群C實行飲食自由之制(即其成員可以自由選擇吃米飯或面包等),而另一人群D則厲行飲食管制,只許吃某一種食品(許食面包而禁米飯,或者相反),那么這兩者是否也構成了不同的“文化”(姑且稱之為文化C與文化D)呢?當然不是!C與D決不是文化之分。這首先是因為A與B、C與D這兩種“文化劃分”是互悖的。在前一種劃分里分屬兩種“文化”的人,在后一種劃分里完全可以同屬一種文化:吃米飯者A與吃面包者B都屬于后一劃分中的“文化”C。反過來說,前一種劃分里同屬于一種“文化”的人,在后一種劃分中也會分屬兩種“文化”。比方說,同為吃米飯者,如果他并不禁止別人吃面包,那他就屬于“文化”C;如果他禁止,則屬于“文化”D。這樣一來,在邏輯上“文化識別”就成為不可能。請注意,這是在邏輯上不可能,不是說的經驗邊界模糊問題。如果一個人既喜歡吃米飯也喜歡吃面包,你可以說他既有文化A、也有文化B的成份,因此很難識別。但這只是個經驗邊界模糊問題,你不能因此說文化識別這件事本身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的確存在著只喜歡吃面包和只喜歡吃米飯的人,亦即文化A和文化B的確可分,盡管亦A亦B或非A非B的情況也不能排除。但如果只吃米飯者自己就可以既屬于此文化也屬于彼文化,而只吃米飯者和只吃面包者又都可以屬于同一文化,同時我們又認為吃米飯者構成一種文化而吃面包者構成另一種文化,那這種“文化識別”還有什么道理可言,還有什么意義可講!
文化識別都不可能,更談何“捍衛文化”?豈止“捍衛”,一切關于“文化”的討論都將成為不可能。因為這種討論將出現更滑稽的悖論:在前一種劃分的意義上提倡文化寬容、文化多元或文化相對論,就意味著在后一劃分意義上只能認同“文化C”而不能容忍“文化D”,即在這一劃分中“文化寬容”之類命題是無意義的。而如果在后一劃分中主張文化寬容(即認可“文化”D的不寬容原則)或文化相對(肯定D與C各有價值,不可比優劣),那在前一劃分中的寬容、相對云云就全成了廢話。為了使“文化討論”有意義,在邏輯上就必須排除后一種劃分。這與討論者的價值偏好無關。你可以喜歡飲食管制,你可以說這種“制度”很好,或者說這種“規定”很好,但不能說這種“文化”很好,否則就沒法跟你對話了。
因此“文化定義”盡可以千奇百怪,但都必須以承認價值主體(個體)的選擇權為邏輯前提。即它只能意味著“我喜歡如何”,而不能意味著“我被要求如何”。我喜歡吃米飯和你喜歡吃面包是文化之別;但我被要求吃米飯和你喜歡吃面包,就決不是文化之別。喜歡纏足和喜歡隆乳,是文化之別;但強迫別人纏足和自己喜歡隆乳,就決不是文化之別。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儒教是文化之別;但信仰自由和異端審判決不是文化之別。喜歡擁戴大賢大德和喜歡擁戴大智大能,是文化之別;但統治者的權力是否來源于被統治者的授予(即來源于后者的“喜歡”),就決不是文化之別。只要不違反這一邏輯,“我喜歡如何”的現實邊界模糊一些也無妨。有人對如今濫用“文化”一詞很反感,如什么煙文化、酒文化乃至廁所文化等,但我以為在這方面不妨寬容些,承認不承認“煙文化”“酒文化”,無非關系到文化討論是雅一點還是俗一點,上綱上線一點還是雞毛蒜皮一點。但如果把自由、人權之類概念都弄到“文化討論”里(象如今一些“后殖民文化”討論者那樣),那就把“文化討論”弄成全無起碼邏輯可言的一堆廢話了。
比方說,我們講滿清入關后強迫漢人剃發易服是一種文化壓迫。現在若有人稱,假如清朝當時不強迫漢人剃發易服,那才是一種更嚴重的文化壓迫,因為他們把“自由”強加給漢人;或者說,漢人反抗剃發易服是一種更嚴重的文化壓迫,因為他們想把“自由”強加給滿人。──那不是胡扯嗎?清初人民的反剃發斗爭是一種捍衛“文化”的斗爭,同時更是捍衛權利與尊嚴的斗爭。而辜鴻銘在民國初年以蓄辮著稱,他并未受到什么干涉,因此其行為并不是在捍衛什么“文化”。這不是說,蓄辮與蓄發有什么優劣之分,也不否認蓄辮代表一種“文化”;而是說,任何“捍衛文化”的斗爭首先都是捍衛自由的斗爭,即捍衛人人有選擇“我喜歡如何”之權利的斗爭。
在已存在自由的條件下,人們“喜歡”的東西(如辮子之于辜鴻銘)無須捍衛就已經有了,而不喜歡的東西(如辮子之于其他人)又不值得捍衛,宜乎“捍衛文化”之說不知何所指矣。只有失去了自由的人們,即不能按自己“喜歡”的那樣作出選擇的人們,才有“捍衛文化”的問題。如喜歡蓄發卻被強制剃發,喜歡纏足卻被強制隆乳,喜歡吃米飯卻被強制吃面包,喜歡敬孔子卻被強制信耶穌等。這時人們起來反抗強制,那就是在捍衛文化(同時也是在捍衛自由)了。在已經有了自由的地方,“捍衛文化”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說,在信仰自由的時代,如果美國有什么人要強制普及新教而禁止天主教,強制普及西餐而封閉一切中餐館,人們會認為他在“捍衛美國文化”嗎?非也,人們會說他在侵犯人權,而且侵犯的恰恰是美國人而不是其他人的人權。換句話說,捍衛文化,就是要反對強制同化,而不是要強制反同化。恰恰相反,文化的捍衛者,必然是強制的反對者,即那些既反對強制同化,也反對強制反同化的人。
總之,我們把“我喜歡如何”的取向,即上舉事例中的A與B之分看作文化之分。而事關能否實現這些取向的安排,即上舉事例中的D與C之分看作制度之分。許多具有同樣的特殊個人喜好的人湊在一起,便成為一種“文化”。憑常識(以及憑我們對人人平等、各個“民族”即各個文化共同體也平等的信念)我們相信文化無優劣,即A與B無優劣。但這就意味著事關能否實現這些取向的安排,即D與C(或曰制度)是有優劣的。區分這兩者很重要,因為人們往往把制度比較與文化比較混為一談,從而產生嚴重謬誤。舉例而言,如今國人似乎已經公認婦女纏小腳為中國“文化”中的糟粕。然而倘若追問,纏足究竟有什么不好?據說是“摧殘婦女身心健康”。但辜鴻銘以昔日西方婦女的束腰陋習同樣危害健康來辯解,不也好像有幾分道理么?近日看到一則報導,說今日西方女性時髦的隆乳術副作用甚大,無論是早期的石蠟注射,還是后來的硅膠、鹽水袋法,后遺癥發生率都頗高,甚至有造成死亡的案例。我不禁想到了辜老夫子,他如果看到這則報導,一定會更加振振有辭了。的確,纏足與隆乳都是以人工夸張女性性特徵來增加“魅力”的“整形手術”,而且后者對健康的危害并不小于前者。那么人們有什么理由在兩者中分高下呢?老實說,在這種問題上我很愿意支持“文化保守主義者”。本人喜歡吃中餐,不喜歡吃西餐;喜歡律詩絕句與古風,不喜歡洋人的“樓梯詩”……
但轉念一想,咱們還是遠離那纏足時代為好,哪怕那“文化”再可愛。其實道理很簡單:隆乳在今日西方是一種個人自愿行為,而過去中國的纏足(與西方中世紀的“貞操帶”等陋習一樣)則是他人強制施行的。正是也僅僅是由于這一點,如今即使在中國,強迫婦女纏足也不為法制所容──這決不僅僅是個審美“文化”問題。而即使在西方,強制他人隆乳也是犯罪行為。同時,那里假如有人喜歡給自己纏足,別人也許會視為怪異,但誰也無權干涉,因為這是她的權利!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纏足與隆乳作為一種個人審美選擇,它是“文化”之別,沒什么優劣可比,更不能把一種“文化”強加給另一種文化的認同者,就象當年西方殖民者強迫土著人信基督教,或者清初滿族入關后強迫漢人“留發不留頭”那樣。但是,強迫還是自愿,是否尊重一個人為或不為某事的權利,則是有無人權之別,當然有優劣的普世標準來加以比較。改強迫之制為自愿之制,無論在哪種“文化”中都應當受稱贊,應當視為可喜的進步。傳統的纏足之所以被今人唾棄,固然也有時尚“文化”變遷的含義,但根本的原因還在于纏足的強制性危害了人權,體現了人類(不僅是中國人)野蠻時代的黑暗。廢止纏足與其說是“文化”的改變,毋寧說是人權的進步。離開了這一點,廢止纏足本身就談不上有什么“進步”意義。
我們知道,明清時代我國南方許多地區對婦女的壓迫并不表現為纏足,而是表現為役使婦女從事比男人更重的體力勞動,因此不僅不提倡、甚至是禁止下層婦女纏足的。“奴婢俱赤足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詬厲之,以為良賤之別。”(民國《陸川縣志》卷4,載《風俗》雜志)這樣的“放足”當然不是什么婦女解放政策。清初滿族統治者在強迫漢族男子剃發留辮的同時,也曾強迫漢人婦女放足。當時規定,若女子違法纏足,其父為官者要撤職查辦,兵民之家要處以杖刑40,再加流放充軍;并且實行保甲連坐,若有纏足而十家長不能稽察,也要打40大板,外加枷號一月;甚至該管督撫以下各級文官有疏忽失察者,也要交吏兵二部議處。然而,漢人對此堅決抵制,畢竟上述處罰還不像“留發不留頭”,人們還頂得住。于是到康熙六年清廷終于不得不解除纏足之禁。這就是后人戲稱漢人對滿人“男降女不降”的由來。然而在今天看來,漢人堅持纏足固然不再那么值得自豪,滿族統治者的強迫放足當然也與自由無關,的的確確屬于一種文化壓迫。可見,纏足與否(或者隆乳與否)是一回事,強迫還是自由又是一回事。前者事關“文化”,而后者事關制度。文化不可比,而制度有高低。以維護無優劣可比的“文化”為理由,阻礙有高低可分的制度之進步,與以改進制度為借口搞文化的強制同化,同樣是毫無道理的。
知榮守辱:文化多元化下,人人都有選擇的權利,是否會導致社會的“囚徒困境”?
秦暉:你說的這個問題即所謂的“群己權界”問題,公民個人權利與公共領域的邊界在哪里,這是個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其他思想流派都有爭議的問題。但對中國來說,這樣的爭議可能還都是未來的事,我們現在需要實現的是在那些毫無疑問(即無爭議地)屬于個人權利領域的地方堅持自由原則,而在那些毫無疑問屬于公共領域的地方實行民主原則;而不是反過來,對個人領域實行“公共權力”干預,而對公共領域又實行“個人選擇”。
蝶之仙:兩句話。一句叫做:“主義”可拿來,“問題”需土產,“理論”需自立;另一句是:弘揚“普世價值”,慎言“普世問題”。第一句我很同意,就不多說了。但第二句只怕有點問題。因為世界上的問題,在不同中有相同之處,在相似中有不同之處。以普世問題的觀點來看待問題,然后再找出區別,應該是一種比較好的方法。但是普世價值,是否存在,本身就應該存疑,更不要說“弘揚”了。
秦暉:“普世問題”當然不是沒有。比如,若有小行星撞擊地球,當然地球上所有人都面臨這一問題。所以我只說“慎言”而不是說不言。但現在的確有一種毛病,就是把別人的問題當成我們的問題。例如,前面提到的“自由競爭太多還是民主福利太多”,顯然就是人家的問題。在人家的爭論中,左翼強調平等,右翼強調自由,而我們難道就不喜歡平等、自由而愛好壓迫和奴役?當然不是。所以我反對把平等、自由之類稱為“西方價值”。
但另一方面,人家那里對個人自由的主要限制是自治工會的力量,或者民主福利制度也許擴張得“過份”了,而對結果平等的主要損害則是,市場競爭和契約自由也許發展得“過頭”。這難道是我們如今面臨的問題嗎?當然不是。所以我反對在我們這里提出削減福利或限制競爭的西方式問題,更反對所謂的“既非自由競爭也非福利國家”的西方式提法。道理很簡單:改革前我們的舊體制就既沒有自由競爭也沒有福利國家,假如反對自由競爭或反對福利國家是我們的真問題,那還搞什么改革?我們如今要改革,不就為的是更多的自由競爭、更多的福利國家嗎?也許將來某一天我們會面臨那種問題,但決不是現在。
然而,如今的確有些人喜歡把西方的真問題變成我們的假問題,藉此來回避我們的真問題;同時又把普世價值說成是“西方價值”,并把從某些俄國人(其實他們也自認是歐洲人)那里借來的價值觀說成是“中國價值”。我把這叫做“錯把杭州作汴州”,就此題目我有一篇文章收在集子里,請指正。我甚至認為:為弘揚普世價值而亟待解決的問題,不僅中國和西方不同,西方各國彼此也差異甚大。如今有人把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或曰“自由右派”與“自由左派”)爭論的那些問題,當成中國思想界的主要問題,這未免太滑稽了。在既沒有保守黨也沒有工黨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都是當年英國自由黨(輝格黨)傳統的發展。而在英國──在歐洲很大程度上也如此──像T.H.格林和E.伯克那樣的自由黨左、右翼并未構成對立,比后者更“右”的保守主義和比前者更“左”的社會民主主義之爭才是社會思想界的基本問題。至于在更為落后的沙皇俄國,甚至英國式的保守黨與工黨之爭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假問題。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言,自由派與社會民主派那時是“分開走,一起打”的,而他們與專制主義、民粹主義的對立才是當時俄國的基本問題!
可見,美國式的“自由左派”對“自由右派”之爭甚至在英國都未必是真問題,更何況在連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爭都還是假問題的中國!